作者:臺灣通傳智庫創辦人 黃采瑛助理教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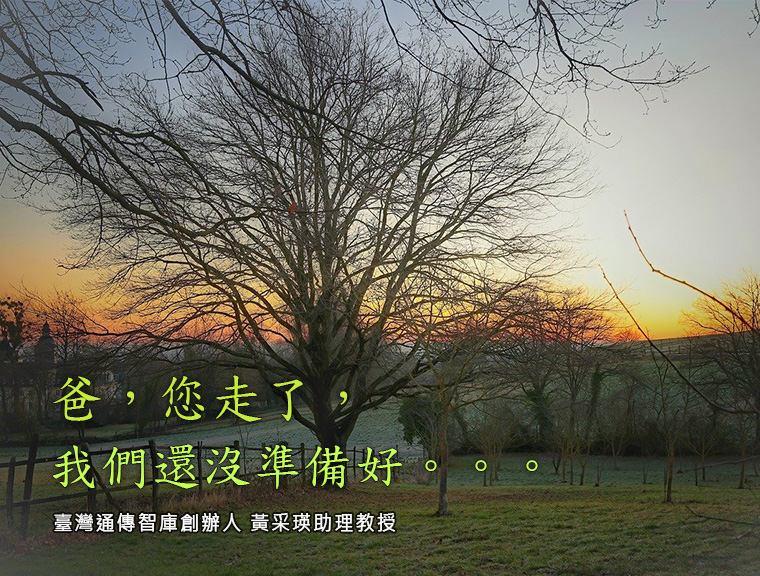
老張,98歲,走了。
他這輩子,年輕時是一名勤奮工作的男人,後來成為一個臥病在床的老人。可惜的是,無論是哪個階段,他都沒有學會怎麼當一個父親。
老張的四個孩子,站在靈堂裡,表情各異。
「這麼多年,我到底是他的女兒,還是他的看護?」 老張的大女兒— 張惠,盯著靈桌上的黑白照片,語氣平靜。但她瘦弱的手指,卻在衣角上捏出了細細的皺紋。
她是唯一一個陪著父親走完最後一程的人。在父親年邁時,已嫁人婦的張惠就守在老張的身旁。直到父親病倒,她又順勢接下了醫院、家中兩頭跑的照顧責任。無數次的夜晚,她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打盹。無數次,她換好尿布,扶著他起身,餵他吃飯,卻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句「辛苦了」。
「他走了,我是不是該鬆口氣了?」這個念頭在她腦海裡浮現,可卻又讓她有著深深的罪惡感。
張家老二張文,站在一旁,雙手插在口袋裡,冷冷地說:「人走了,大家就該開始說他好話了,對吧?」
老張年輕時有過一段婚外情,這件事,在張文十歲那年,變成他人生的轉捩點。他永遠也沒有辦法忘記─ 該夜,他看到媽媽坐在廚房的燈光下哭,看到爸爸帶著疲憊,但不帶歉意的表情回家。然後,家裡的一切變了。媽媽變得沉默,爸爸變得更加專注於工作,仿佛家是一個可以住,但不必經營的地方。
媽媽走得早,張文覺得,是爸爸害的。
「一輩子工作,然後病倒,連最後一程也是我姐照顧的。他到底把我們當成什麼?」 他低聲說。
老三張俊,從小是家裡最會察言觀色的人,現在則是沉默地站在角落,雙手交握在胸前。他是最少抱怨父親的人,因為他早就不期待了。他覺得這個家像是一個商業合作關係,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。父親掙錢,母親管家務,孩子各自長大─ 各自承受自己的痛苦,沒有人真正連結過。
但此刻,看到靈桌上的遺照,他的心裡有一絲說不上來的複雜感。
「他曾經也是個年輕人吧?是不是他也有過想要溫暖我們,卻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?」
小妹張婷,是家中的老四,亦是最早搬出去住的人。
爸爸過世了,她的朋友在LINE上安慰她,她卻打出:「沒什麼特別的感覺。」然後,又刪掉。
因為,她知道自己不是沒感覺,她只是害怕去感覺。
她年輕時,一直努力想得到爸爸的認可。可是,無論她多努力,爸爸永遠都只會淡淡地說:「這是應該的。」長大後,她學會了不去在意。但現在,他走了。她卻發現,原來她還是很在意!
四個兄弟姊妹,站在同一個靈堂裡,心裡裝著不同的心事……。
其實,哀傷的歷程非常複雜
一般人以為,親人的過世帶來的只是「思念」。事實上,哀傷(grief) 的本質,是對未完成的「情感帳」的真切反應。
心理學家 J. William Worden 提出了「哀傷的四大任務」理論(The Four Tasks of Mourning),比起單純的「五階段哀傷模型」,這個理論更能幫助我們去理解─ 當一個親人離開,我們真正面對的,是什麼樣的心理課題?這四大任務包括了:
- 接受現實(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loss)
「他真的死了,這件事已經發生了。」
這代表著:我們得接受,他帶來的傷害,也不會再有機會彌補了!
這對大哥張文來說,是最難的一件事。他一直覺得,父親沒有真正彌補過母親,沒有彌補他們。現在,父親死了,他連「向他討回公道」的機會都沒了。這讓他無比憤怒,但又無比無力。
所以,真正的接受父親離世。其實,不只是接受死亡,而是要能夠接受「那些遺憾,可能永遠不會有解」。
心理學的諸多研究顯示,壓抑情緒會讓人困在傷痛裡。是故,張文可以允許自己承認:「我還是會覺得憤怒,還是會覺得不公平。」 這些情緒不是錯的,只是需要被解決。
因此,他可以找個安全的出口釋放情緒。比方說寫一封信給父親,把所有的憤怒、失望寫出來,一同火化。同時,允許自己討厭父親,但不讓這個討厭決定自己的人生。亦即,與其一輩子被「不公平」綁住,他可以以積極的作為,做出「我不要變成像我父親那樣的人」的選擇。
- 經歷痛苦的情緒(Process the pain of grief)
大姐張惠,這幾年累積的不是單純的悲傷,而是疲憊、責任、和難以言喻的矛盾。她愛這個家,但也恨自己被困在這個家。父親走了,她感到內疚,因為她有一絲鬆了口氣的感覺。
這種「照顧者的罪惡感」,在心理學上很常見。她需要允許自己去承認:「我可以覺得鬆了一口氣,這不代表我不愛他。」
- 調整與亡者的關係(Adjust to a world without the deceased)
這不是指「忘記」父親,而是要改變我們與他的心理連結方式。
例如,老三張俊一直習慣讓自己與父親在情感上保持距離。但是,當他開始回想:父親或許也曾有想靠近家人的時刻時,他的心境便隨之開始產生了變化。他可以選擇繼續當一個「與父親沒有交集」的人,或者,試著用新的方式理解他。
調整的方式,可以是重新定義這段關係,例如:透過寫信的方式,把想對父親說的話寫下來。或者是,找一個儀式(像是整理他的遺物,或是跟家人分享回憶),來建立對父親新記憶的心理連結。
- 找到新的意義,繼續生活(Find a way to move on while keeping the deceased in your life)
老四張婷一直想得到父親的肯定,現在他走了,她再也等不到那句「你做得很好」。但她可以問自己:「我要如何定義自己的價值,不再需要父親的認可?」
她的「放下」不是不再想起父親,而是讓自己不再受限於「爸爸怎麼看我」的影響。
有時候,最難的不是「失去一個人」,而是「這個人帶來的遺憾,沒有機會再被解決」。但心理學告訴我們,哀傷不是一條線性的路徑,而是一種適應的過程。我們不需要「放下」,我們需要的是,學會如何與遺憾共存。而這有時候,並不是靠時間讓我們沉重的心變輕,而是靠我們找到承載憾慟的方法,好好安放受傷的自己。
